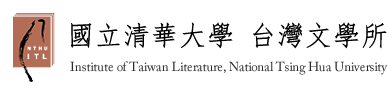2017年第十三次例會
台灣文學研究會第十三次例會側記
紀錄者:姚旟荃
陳芷凡教授開場
台灣文學研究會自 2012 年籌辦第一屆,經過多年的努力直至今天舉辦第十
三次例會,本會籌辦的初衷是希望能夠結合更多跨校且跨領域的學者,一起來思
考如何讓文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讓台灣文學的研究發展出新的期待。
此次議會的主題是由本所同樣從事翻譯研究關切的王惠珍老師進行統籌,並
且邀請此次與會的三位講者,而這三位講者既是研究學者也是翻譯者。單德興老
師是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研究的領域為比較文學、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
與翻譯研究,而除了文學與文化論述之外,單老師也翻譯《知識分子論》及《格
理弗遊記》等譯作,同時肩負研究者以及翻譯者的挑戰與責任。李育霖老師為中
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台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所的所長,研
究的範圍是電影研究、生態批評和德勒茲研究,譯有《德勒茲論文學》、《德勒茲
論音樂、繪畫與藝術》等,李老師是將德勒茲這位理論家的論著與理論概念介紹
給台灣讀者的重要推手。廖詩文教授是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副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翻譯理論、中日比較文學還有影像翻譯與視覺文化,廖
老師近來關切的議題是日本重要的文學家,例如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以及三浦
綾子文學在台灣翻譯的情形。
在惠珍老師的促成之下,這三位本身從事翻譯,同時也是翻譯理論傑出且重
要的研究者聚集在這裡,一起就翻譯文學與跨文化的命題展開更多元的對話。
一、單德興教授—談譯者余光中以及華美作家哈金
翻譯之必要,譯者之必要
余光中老師因為詩歌和散文的成就高超,以致許多人都忽略了他身為譯者的
貢獻。余老師提及譯者的時候曾說,「譯者未必有學者的權威,或是作家的聲譽」,
但是他特別推崇「翻譯」以及「寂寞之譯者獨享之特權。」然而,他也指出一般
譯者的實際情況卻是「往往名氣不如作家,地位又不如學者,又常常無利可圖,
而且稿酬偏低,無利可圖,又不算學術,無等可升,似乎只好為人作嫁,成人之
美了。」在場的三位講者都曾翻譯過專書,對於以上的說法應該特別能夠感受。
根據單德興老師(以下稱為講者)的經驗與理念,翻譯不應該只是文字的翻譯,
也應該把文字、文本之後的相關文化、歷史脈絡帶入其中,也就是原作、作者及
其脈絡的關係之外,還有進入另一個文化時可能產生的新意或效應,這也就是他
所提倡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的觀念。
在陳芳明老師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所編的余光中資料彙編1 中,談到余光中與
翻譯的只有金聖華老師的〈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譯家〉,由此可見對於譯
者余光中的相關研究非常少,而講者這幾年特別著重在這方面,已發表數篇論文
與一篇訪談。余光中老師除了身為學者、譯者、作者三「者」合一之外,張錦忠
1 陳芳明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34:余光中》(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也提到他是「五譯並進」:做翻譯、論翻譯、評翻譯、教翻譯、編譯詩選集。講
者則補充了另一譯,指出余光中老師多年對於翻譯的提倡不遺餘力。
從 1956-1957 年的《梵谷傳》2一路到王爾德所有的喜劇、2012 年的《濟慈
名著譯述》等,余光中老師的「譯績」多元而繁富。就譯出語與譯入語而言,既
有英翻中,也有中翻英;就文類而言,既有詩歌,也有小說、傳記;在工作方式
上,主要為獨譯,但也有合譯;有他譯,也有自譯;有單篇發表,也有連載、出
書;既有單一作家的文本,也有合集;既有他選,也有自選;既有中文文本,也
有英文文本,以及中英對照本;既有縱貫數世紀的詩作,也有十九世紀經典美國
文學,以及現當代的美國小說與中、英文詩作。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翻譯家的
養成不易。他的譯詩相當多元,從翻譯英詩中學到的內容、意象、形式都對年輕
詩人余光中有相當大的啟發。他自己也提到翻譯與創作之間密切的關係,主張譯
者要努力兼顧譯作的形與義。至於翻譯當中的歸化與異化,余光中比較傾向於歸
化,但也不全然排斥異化,因為異化能增加中文的表達方式。此外,他很明白再
好的翻譯也是能挑毛病的,因而提出「譯無全功」之說(Translation knows no
perfection.)。余光中從事翻譯工作將近一甲子,這種毅力與堅持非常值得我們敬
佩與學習。
哈金出生於中國遼寧,快 20 歲才開始學英文,1984 年取得山東大學英美文
學碩士學位,1985 年赴美留學,1992 年取得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博士學位。1989
年因為天安門大屠殺而決定留在美國,並選擇以英文從事文學創作,其後陸續獲
得美國眾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學獎項。身為使用非母語寫作的創作者,哈金先是出
版詩集,直至 2015 年才出版第一本中文詩集《另一個空間》。在例會中講者把哈
金的小說與譯作列出,並且提出了為何哈金未被納入台灣文學研究當中的疑問。
翻譯能不能列入 Sinophone studies(華語語系研究)?講者作為一個譯者以及翻譯
研究者,希望能夠從不同角度以翻譯來介入文學,一方面擴大文學研究的視野與
領域,另一方面也擴大翻譯研究的視野與領域。在哈金的漢譯作品中,有他譯、
自譯以及合譯,即使大多為他譯,但哈金都參與校訂,由此可知他在翻譯自身作
品當中的介入甚深。就他的身分來說,說他是華裔美籍作家、離散作家應無疑義。
但他能算是華語語系作家嗎?講者主張要將其放入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脈絡
中,這樣能夠 Sinophone studies 的領域擴及中譯的文本。那他能夠算是中國作家
嗎?講者舉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例子說明。中共官方主張高行健不是中國
人,法國人則是欣然接納高行健為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哈金的作品都在
台灣翻譯、出版,在大陸卻大都被禁止,那他能夠算是台灣作家嗎?單老師留下
這個課題等待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者來思考。
講者接著提到翻譯文學研究中多元系統(polysystem)的問題,特別是翻譯文
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當翻譯文學並非處於華文文學的首要或中心位置時,
哈金的作品依舊不斷地被翻譯成中文,因此華文世界對哈金的青睞是不能否認的
事實。如果翻譯作品在華語文學中有如一道光譜(spectrum),講者提出四項判準:
2 《梵谷傳》上、下冊分別於 1956、1957 年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作者是否為華人,二、寫作題材是否與華人有關,三、作者是否通曉華文,
四、作者在其作品翻譯過程中的介入程度。這四點將中譯文本納入 Sinophone
studies 的標準做了定位,而以這四個條件來看,哈金的作品確實能夠納入
Sinophone studies 當中了。
翻譯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關係,講者舉自身翻譯的《格里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為例,林以衡博士在做相關研究的時候,翻閱台灣日據時期的報紙發現
《台灣日日新報》就已經翻譯〈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而且報上還有序言,
這就代表此書的翻譯很早就進入台灣了,而且若非台灣文學研究者的努力,大家
就沒辦法注意到。
最後單德興老師提及理論的旅行與翻譯問題。陳芳明老師曾說「盡信理論,
不如沒有理論」,而講者則進一步主張「盡信理論,不如了解理論」。講者在翻譯
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文本時,將其理論的翻譯帶入華文世界的脈絡中,
希望薩依德的翻譯在中文世界不只是一個譯本,而是能夠確實向下扎根。賴慈芸
老師也將戒嚴時期的台灣翻譯史作了追蹤整理,完成了《翻譯偵探事務所》。3 講
者進一步表示,譯者的角色包含了中介、溝通、傳達、介入、操控、轉換、背叛、
顛覆、揭露與掩蓋、能動與反間、重製與取代等等。譯者不只是再現原作,也再
現了自己;而譯者同時也是益者,因為好的翻譯對作者、讀者、雙方文化和譯者
本身都有益處,是連結兩個語言與文化之間的橋樑。單德興老師強調台灣的比較
文學若要再出發,必須加強台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匯通,開啟彼此更廣闊的視野
與願景。
二、李育霖教授—談 Sinophone/Sinoglossia 的問題,以夏曼藍波安為例
台灣文學作家因為被殖民的關係,一拿起筆就活在翻譯當中,而做為一個第
三世界的人民,當書寫時本身就有翻譯的難題,而翻譯帶出來的,則是台灣文學
美學風格以及主體構成,甚至是倫理、或是如何生存的問題。而李育霖教授(以
下稱為講者)要談的是關於 Sinoglossia 的問題。從 Sinophone 開始談起,Sino 本
身就帶有殖民遺產命題並與之連結,而李育霖教授將 Sino 譯作為「華」,本身與
Chinese「中國」區分開來,也就是 Sinophone literature 與 Chinese literature 兩者
的區別。兩者在北美學界的脈絡中,已有區分,而所謂「語系」也與 Mandarin(普
通話)或是漢語的指稱不同了,這樣的論述同時也帶有中心/邊緣
(central/peripheral)、統一/碎片(united/fragmentary)、統一性/延異性
(unity/divergence)等對偶關係。這樣看來,史書美 Sinophone 的概念在台灣與後
殖民的概念連結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依舊充滿爭論,而王德威老師所談論的
Sinoglossia(華夷風)的概念,則是從中華文明脈絡一貫而下的華夷之別。
講者則是期待能夠從語音的角度將聲音放入 Sinophone 的文字當中,強調音
與文字之間的張力,不管文字是哪一種,於是他企圖發展 Sinoglossia 的論述。
Glossia 也就是拉丁語當中的語言的意思,Heteroglossia 眾所皆知的巴赫汀的眾聲
3 賴慈芸,《翻譯偵探事務所》(台北:蔚藍文化,2017)。
喧嘩,當中強調語言不是單一的,而是有所謂分歧的力量,這個分歧理所當然的
有一個中心(例如政府的規範),而日常用語當中又有離心的張力;而 Hetero 則同
時有傅柯的異托邦的概念在其中。講者企圖用此發展出 Sinoglossia 的雛型,而
glossia 指的是語言以及聲音本身,也在這裡我們從這裡看到翻譯的介入,
Sinoglossia 不只是語言的問題同時也是翻譯的問題,因此講者將 Sinoglossia 翻譯
為「華迻論」,這個「迻」字有翻譯的意思,包含了時間上的遷徙、民族的遷徙
以及跨國性的遷徙,而在《說文解字》中,「迻」則有翻譯(迻譯)的意思,他
再度強調 Sinoglossia 是一個語言的問題,同時也是翻譯的問題。
那如何看到翻譯呢?翻譯從字元來看就是把一個語言放在另一個脈絡當中,
是一種搬運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種重複。當我們在讀譯本的時候,即是一種重
複,在講者的認知當中翻譯是一個事件,是一次的重複性而不能被約化成一種再
現而已,而是一個行為。另外也要注意到翻譯的必要以及不可能。講者繼續以夏
曼藍波安為例,說明翻譯的相關問題。夏曼將達悟語與中文並列產生怎麼樣的效
果呢?兩種文字各自獨立的並列,並不直接指向中文翻譯,相反地,將讀者引入
一個巨大的空白、完全陌生的世界。
翻譯如何介入夏曼藍波安的書寫呢?先將中文文字放進括弧當中:「katwan,
katwan」 (飛魚,快來呀!快來呀!),或者是先用中文寫出達悟語,後再括弧
用中文解釋:「老人的太陽很低了」(歲月催人老,往事不堪回味),這樣的翻譯
介入成為一種雙語的不斷錯位詮釋,還有另一種「交換式的翻譯」:「我肉體先前
的靈魂」(先父,先母),成為達悟語的特殊用法在中文當中文字的轉換,而更深
一層交換,例如“mi kongkong si “ (達悟語,被恭喜之意),可以看到恭喜的意思
介入了達悟語當中,這些交換的過程不只是語言上,而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交換。
而翻譯當中的 Translingual(所謂的跨語的實踐),表現出來的是跨語的書寫,在翻
譯當中是一種結合、糾纏、混雜的表達,包含了字彙的、構句的、句子的、文法
的融混表達,舉例來說:「許老,海流會帶你回大陸。Kak mamoayayipasalaw so
pahad. (願你的靈魂如燕子般的善良)」,這個構句就是上述許多翻譯的作用,
也是跨語的實證。而在語言與文化上的接觸和衝突則是在《老海人》當中,國民
政府要求達悟耆老慶祝雙十國慶的情況更為明顯,那些「中華民國萬歲」式的吶
喊對達悟耆老來說是陌生的、無法理解的語言,於是以鬼吼鬼叫來呼口號,彼此
聲音的不協調成為一種聲音與吶喊的對峙,對彼此來說都沒有內容的聲音,因為
無法與語意做連結而造成衝突,翻譯者在這裡的作用則是粉飾雙方的語言並且弭
平衝突,雖然看似縫補語意的裂縫卻也擱置了文化的衝突。
三、廖詩文教授-談朱天心的《古都》日譯本
廖詩文教授首先談台灣文學的翻譯問題,他不只是關切外國文學在台灣的影
響和發展,也關心台灣文學輸出的議題,於是做了公部門外銷台灣文學的考察,
發現文建會時期和台灣文學館時期的公部門外譯情形有些不同。文建會時期外譯
推廣的文學類型包含了中國文學(例如史記等),且以英文譯作為大宗,並有較
多男性作者的作品,而台灣文學館接手後的外譯作品,則以日文較多,並以具有
更強的台灣文學主體意識作品為主,女作家作品也占了大部分,顯示出外譯至日
文的作品和英譯本在選書的考量上有所不同。講者提到這與翻譯贊助人、意識形
態、政治等等的因素有關,種種因素皆會導致英文讀者與日文讀者對台灣的想像
有所差異。而這也使得講者開始注意女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在日文當中被再現與
翻譯。
《古都》是記憶之書,以個人記憶納入歷史的記憶,是朱天心構築的烏托邦
世界,與川端康成的《古都》同名,那這兩者的互文性當然是在翻譯過程當中需
要注意的。這裡的互文性不只是出現在書名上的互文而已,內容上,包含地景、
生活上的描寫,朱天心的《古都》也都不斷與川端康成的《古都》互文,小說的
「虛構」與其外的台灣地景地物存在的「真實」也不斷互文。可想而知,譯者在
翻譯時就必須先對川端康成的《古都》有所了解、對朱天心描寫的台灣地景變遷
有所認識,方能翻譯得好。
清水賢一郎作為朱天心《古都》唯一的譯者,在翻譯時,展現出他仔細考證
朱天心文本內容的專業性。清水賢一郎的翻譯,段落上採原文尊重主義,在形式
上並未更動原文的結構、段落的再現,而在遣詞用字上,則採譯文尊重主義4,
使日語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能更容易理解句意。雖然某些地方並非直譯,但是保留
了原文的意象,使得譯文在日文當中更為流暢,而若是原作中獨特的台灣地景、
時空等等的描寫(對日本讀者來說的異文化),清水賢一郎便會保留並加以標音,
讓朱天心的異文化互文風格更為突出。此外,清水賢一郎在日譯本上增加許多譯
註,使《古都》日文版在考據上顯得更為細緻,甚至可以作為原著的參考書目。
《古都》日文版與中文版是用一種鏡像互文的方式,將朱天心的《古都》順
序重新排列,成為作者與譯者共同記憶的鏡像反射,而因朱天心又與川端康成的
小說內容彼此互文,這三者於是成了多菱鏡的折射關係,篇章的重新排列,使得
譯者也在翻譯上凸顯了其譯者的身分。
此外,因為日文沒有未來式,而是會在需要之處,或以現在式表達未來,或
用現在式表達過去,或用過去式表達時間,但這些時態與時間其實並沒有直接關
係,因此在翻譯的同時,譯者需要清楚了解原作中時間的穿越關係、空間的位移
關係,這樣才能使得日文句式準確表現出原作的語意。日文句子上主體改變的同
時,某些時間就會變動,再加上日文當中的主體若是遇到第一、第二人稱的時候,
往往可以加以省略,於是你/我的分界也會更模糊,中日語言結構上的差異性,
在碰觸到刻意模糊你/我身分與喜愛穿越時空的《古都》原著來說,日文譯者如
何掌握譯本的時態句構,就成為值得關注的研究項目,特別是在原作與翻譯間必
然存在詞語、句子不對等與無法跨越的難題上。
講者特別強調日本在進行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時,有時會從觀察譯者採用譯
文尊重原則還是原文尊重原則的方法切入。上述的觀點,與異化或歸化的分類略
有不同。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實務上往往無法全採異化或歸化的方法,而多是在
4 譯入語文化怎麼表達,就怎麼翻譯。
尊重原文或尊重譯文的原則下,透過譯者的巧思,適當傳達原作所要表達的意象;
而在翻譯之間發生哪些變化、為何如此變化,則就值得探討而成為比較文學研究
上關心的「有趣」議題。
透過《古都》譯本的解析,譯者表示除了可以看出朱天心在原作上刻意把你
/我、你們/我們刻意模糊化的書寫技巧,也可看到日文因須釐清主詞才能清楚
指陳作品中所要表達的主題,因此在譯本上,你/我、你們/我們反而在某些時
候必須被凸顯出來。這也會造成日文讀者和中文讀者在賞析《古都》時,分別會
有不同的閱讀樂趣及體驗,同時也讓我們再次確認了在不同語言的轉換上,主體
敘事會因不同語言表現而有難以跨越的藩籬。但在《古都》譯本上,譯者的考察、
對原作的深入、譯註的撰寫,確實讓日語讀者更容易了解作品的內容。
重點討論
王惠珍老師:針對李育霖老師談到夏曼藍波安的文本,夏曼的文本其實也有日譯
本,那日譯本是如何去翻譯夏曼的語言,翻譯再翻譯的問題要如何詮釋,這變成
了一種重譯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說,葉石濤先生在翻譯韓國文學的時候他並不懂
韓文,但將日本學者翻譯韓文的文本再翻譯成
卜生為例,他本身寫作的挪威語是個小語種,所以很多國家翻譯他的作品都是透
過英譯本,這是不得不的作法。另外,就目前的國際市場來說,很多翻譯作品都
是先有英譯本,在參加國際書展引起其他語種的出版社注意後去接洽版權,而後
再從原文直接翻譯成英文之外的語文,所以雖然還是直接從原文翻譯,但卻是透
過了英文的中介。其次是理論的翻譯,現在很多文學與文化理論都是來自大學出
版社的英譯本,理論上應該比較可靠,其實未必。這裡舉兩個例子。一個就是李
歐塔的《後現代情況》(Francois Lyotard, Postmodern Condition)英譯本,有熟
悉內情的歐洲學者告訴我,這本書上掛了兩位譯者的名字,實際上兩人根本沒有
合作,而是原譯者的翻譯不能用,只好使用後面譯者的譯本,但又不能讓原譯者
感到白費工,所以掛了兩個名字。另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就是,彭淮棟直接從德文
翻譯《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Beethoven: Philosophie der Musik [Beethove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並在〈譯跋〉寫到,雖然他直接譯自德文,但在參
考英譯本和簡體字版的中譯本時發現,英譯本中的誤譯(否定詞沒有翻譯)導致
從英文轉譯的中譯本也隨之誤譯。因此,彭淮棟必須特別在〈譯跋〉中指出來,
免得別人對照英譯本而認為彭譯是誤譯。此外,柳書琴老師剛剛跟我提到,有佛
教團體要將藏文佛經翻譯成中文或英文,而藏文佛經本身是從印度梵文翻譯,梵
文的原文可能早就不見了,所以原本是譯文的藏文佛經就成了唯一的原文,再翻
譯成中文或英文時就變成是再翻譯。中文裡也有類似的情況,比方說梵文經典翻
譯成中文後,原來的梵文經典迭失了,或者也許還在但已翻譯成藏文或英文,若
要比對的話需要具有多語文的能力,所以牽涉到翻譯或再譯的情況。最後一個例
子是,我翻譯聖嚴法師在美國主持禪修時的禪堂中文開示,一方面是法師將禪宗
祖師大德的文言著作翻成白話,這就是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另一
方面是現場有專人口譯成英文,又牽涉到口譯(interpretation)與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後來經由錄音之後的整理謄抄,從語音文本變成文字
文本則是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之後編輯出版成英文書,再由筆
者翻譯成中文書,所以這裡比剛剛說到的重譯或轉譯更加複雜,既涉及中翻中的
語內翻譯,也涉及中翻英與英翻中的語際翻譯,更涉及返譯(back translation)
或雙重返譯(dual back translation)。因此,翻譯是變化多端的藝術,而這也是
翻譯好玩、有趣的地方。
李癸雲老師:從李老師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夏曼‧藍波安在創作的時候,是
先用達悟與寫下他想寫的之後再翻譯成中文,那他到後期比如說《老海人》這樣
長篇的著作一樣也是用同樣的創作方式嗎?或者說他常常在臉書發表自己的看
法,連這樣子的創作方式也是透過翻譯嗎?那假設他必須都要通過這樣的程序的
時候,李老師也提到就是說,達悟族的語言有它背後的一些思想、文化甚至祖靈
信仰、種種的語音等很特殊的表達方式,可是當他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夏曼只能援
用他如何被中文這個語意系統所訓練的東西來翻譯,所以他用的是華語或者中文
的邏輯、文化等,那當然你肯定在翻譯過程當中,可能有滲透的部分,尤其是在
語音滲透或者是用語的變異等等,可是如果我現在又是一個讀者在介入這個過程,
閱讀理解這些作品的時候,是不是也是一種意義的翻譯?那這個讀者如果不是跟
夏曼在相同的達悟思想底下的時候,他所能萃取到或理解的或許都還是這個讀者
背後中文的語言系統而已,所以如果他有變異性或是被滲透、被改造華語的可能
的時候,會不會其實都被阻隔在文化差異之外?也就是說夏曼的那一套中文的使
用方式只能停留在夏曼,如果沒有跟他有相符合的、了解達悟的表意方式的人,
他所能理解的可能還是從中文的角度去看,而沒有去察覺那些特殊的、屬於達悟
族的東西。
李育霖老師:我簡短的回應一下。你覺得他寫的是(標準)中文嗎?你說,你用
中文的角度去讀,那你覺得夏曼寫的是中文嗎?
李癸雲老師:中文這個介譯是字符的問題嗎?
李育霖老師:這樣就變成如果你要去判斷什麼是中文,然後說夏曼是或不是(中
文書寫)?我剛剛講說,特別是在《八代灣神話》等剛開始創作的時候,因為他
對中文沒有把握,對達悟族語也沒有太大的把握,但是他寫的過程他自己講說他
還得必須用達悟族語寫下來,然後再翻譯成中文,因為他中文也沒有把握所以非
常的痛苦,這是早期的呈現。但你可以發現,他寫作的策略或者是翻譯其實是有
改變的,有時候他用翻譯的方式,有時候他用並列的方式,我想並列的方式有一
段期間,特別是他參加原住民運動的時候,意識到語言本身就標示著文化區位的
存在,所以他很刻意在中間那段創作時間特別都是用達悟語並列的。在早期其實
那樣翻譯是更明顯的,因為他嘗試把所有達悟語翻成中文,所以他很懊惱為何當
時不是用達悟語寫,所以這二三十年的創作他的內在其實是有變化的。
回到最後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他做為一個華語表述的形式,在形式上它產生
了變異,在語言內部或是書寫的符號本身都產生了變異,這是我的結論。至於你
剛剛的問題,如果你有所謂的標準的中文,那你就可以看到屬於變異的部分。就
像我剛剛講的,中文是分歧的、碎片的、在變異當中的。我並不像後現代主義者
去標榜一種語意或者符號的漂流,譯文仍然是對應原文,原文跟譯文之間就算我
們不知道原文,但像夏曼‧藍波安的文本,我們能夠在譯文中間看到原文,很多
台灣文學或理論是沒有原文的譯本,因為我們寫的是華語,但不是母語,所以原
文在譯文中,我們還是能在譯本當中讀到原文,所以原文跟譯文在生產中是不斷
交錯、摺疊的過程,這個摺疊的過程會產生新的東西。至於讀者能不能介入這樣
閱讀過程當然是可能的,像現在網路,或者是現在強調互動,我覺得這是個新的
領域,我目前還沒有辦法掌握那個部分,我想以此作為出發點,在所掌握的符號
或聲音裡面觀察到它的變異,去判斷台灣文學當中的特殊風格跟他內部的主體構
成,我想這是我關懷的重點。
許宸碩:老師你剛剛有提到翻譯的問題還有台灣文學,我就想到台語羅馬字,台
語羅馬字在華語語系當中會談到這個特殊的例子嗎?台灣之所以有很多文本翻
譯到日本,還包括兩國之間的政治互動,我們翻譯外語的時候是需要理論的輸入,
那我們有華語知識的輸出嗎?
李育霖老師:的確,在華語語系的研究當中的確沒有注意到台語羅馬字的問題,
但在華語語系研究當中,我們不是去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華語語系、那個東西是
不是華語語系,因而把華語語系視為一個範疇。對華語語系的看法各有說法,但
台語羅馬字是不是華語語系,如果你覺得是的話你就去談談看,如果不是的話也
可以談,有些人認為華語語系的基本定義是所謂 Written in Chinese,根本的定義
是用中文寫的,那剛剛單老師也提到用英文寫的能不能算入華語語系,那當然如
果算入的話,定義就會改變,可能是一種族裔或者文化的概念了,所以重點不是
什麼東西是 Sinophone,重點是你的東西用 Sinophone 可以帶出什麼命題和什麼
思考的力度。
第二個知識輸出,我講個例子我與前輩老師聊天的時候常常提到,例如日本用四
代完成現代化的過程,第一代包含出去(出國)學習並且翻譯回來,第二代用外
國理論認識(本地的文本材料),第三代發展出自己的東西,第四代再把理論輸
出。回到台灣的知識輸出,史書美老師現在與一群學者在做的是台灣知識系統的
建構。我們的確是做為一個殖民地,我們吸收很多外來的東西,也派很多人去國
外輸入,所以覺得我們這一代特別辛苦,一方面又要翻譯、一方面又要拿西方的
東西拿來研究台灣的東西、一方面又要把台灣的東西搞出理論、再來又要把台灣
的東西提高國際能見度,所以四代的事情要壓縮在這一代完成。所以講說有沒有
理論輸出,西方正在很快速的輸出,那台灣必須更加緊速度來推動我們的思考、
知識系統或是思維方式。如果台灣的思維方式是特殊的,那自然世界就會來參考,
台灣的確在經濟歷史都有特殊的案例,所以都會有外來者來研究,台灣確實在很
多方面都不是太重要,但就是因為這個不是太重要在很多方面不佔有主流的知識
範圍當中,所以我們能夠創造出新的模式,這是我們社會所要追求的東西,我講
的很快而且夾帶著很多民族歷史的情感在裡面,但這是我們這一代承襲陳萬益老
師那一代的工作。
陳萬益老師:稍微來談台文所在講翻譯的問題,歡迎三位來台灣系所講比較文學
講翻譯等等的問題。那單老師剛剛在過程當中,可以說是向台文系所師生挑戰,
也可以說是在翻譯理論底下來談台灣文學的課題,那我先回答你台文系所有沒有
在做翻譯的研究,我沒有全面去了解,不過清華有一個碩士論文,是做日本時代
台灣翻譯的研究,比較具體的,他是拿賴和、楊逵、張我軍他們一批人來討論的,
賴和的翻譯他有翻譯尼采論文,大概是在他醫學校時候所作的翻譯,張我軍因為
後來他到北平,他的翻譯相當的多,因為他也從事日語的教學嘛!其中有一部我
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夏目漱石的文學論,這部書到台灣以後還沒有出來,也沒有看
到別的精通日文的人來翻譯這部書,據了解這是夏目漱石在那個時代,日本近代
文學史當中很重要的文學論,那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說,賴和在 1924 年跟張我
軍引發起來的新舊文學論戰當中,賴和就說過,「新文學是舶來品,所以帶有奶
油的味道。」。這個也就是那個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接受到外來
的思潮,外來的作品影響,開展了新文學的寫作。所以陳千武就說了台灣新文學
的兩個球根,在過去的幾個世代裡一直就講台灣新文學受五四影響,這不必否認,
但他另一個球根其實是從日文來接觸的外國文學的影響,所以前不久受到相當注
目的,講 1930 年代風車詩社,這個也是逐漸被發現整理出來的,原來我們台灣
在 1930 年代就有一個這樣的相當現代主義的詩社,有他們創作的成品,所以不
僅是在日本時代這一批在日本教育底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以至於到戰後,其
實他們也還在做翻譯,所以在台文系所當中作翻譯研究不是不可能,也是應該重
視的面向。
第二個問題你談到哈金,然後 Power point 當中你明顯的問說,到底哈金是中國
作家還是台灣作家?我想先請問你最後的結論。
單德興老師:我想這可能要留給各位台灣文學的專家和後起之秀來回答。如果容
許我舉一個例子。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中提到張愛玲,那張愛玲算不算台
灣作家?我想先請教您的意見。
陳萬益老師:因為你講哈金接著提到高行健,高行健曾經來清華大學做過專題演
講,柳書琴老師主持的,那場在清大大禮堂九成五都坐滿,從高行健談起。高行
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接到一通國外來的電話,韓國打來的,我台大的學
弟打電話來請我以最快的速度寄高行健的書給他,因為高行健在中國大陸基本上
是封殺,不承認他是中國作家,但是國外還是在看高行健,是看明星出版社出版
的作品,所以高行健我就說是台灣作家,如果是這樣講的話台灣作家就得到諾貝
爾文學獎了,這當然是開玩笑的。但是,你剛剛提到張愛玲是不是台灣作家的問
題,在 1999 年聯合報副刊選台灣經典 30 家將張愛玲選進去,後來陳芳明在經典
30 之後的會議也說張愛玲是台灣作家,台灣與會人強烈的抗議說張愛玲不是台
灣作家,為何聯合報將他選入台灣的經典,這個問題在台灣文學界一直議論紛紛,
當然你看到陳芳明的新文學史也寫進張愛玲,但被稱為台派的文學史經典葉石濤
的《台灣文學史綱》也把張愛玲寫進去,更特殊的是 2000 年成大台文所,葉石
濤先生在那邊講課,我們的客座教授下村作次郎就去聽、去錄音,有一天葉老講
張愛玲,下村跑來找我:「陳老師,葉老說張愛玲是台灣作家。」,我說怎麼可能,
他就把錄音帶給我聽。這個話題確實在 2000 年才開展起來的,台灣文學的體制
化作為一個新興學術領域當中,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斷,所以學生也會問我張愛玲
是不是台灣作家,我說當然不是啊,她怎麼會是台灣作家呢?但是台灣文學史有
寫進去啊,那為什麼他不是台灣作家?今天你今天講的剛好可以回答。哈金他是
中國作家還是台灣作家?還是華裔美籍作家?高行健是華裔法國籍的作家?如
果中國人高興說他是我們中國作家,如果台灣人因為他的書在台灣出版所以說他
是台灣作家,隨你高興啊,有什麼不可以?艾略特是美國作家還是英國作家?都
可以。就是說只要國人認同,他就是你的作家,如果我們往前推,台灣文學史的
寫作一開始就沒有問「你是不是台灣作家」,黃得時在 1943 年台灣文學史的序說
當中就這樣說,台灣文學史要寫哪些人哪些作家,他有一個關鍵詞叫文學活動,
文學活動在台灣的就把他收進來,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說,張愛玲絕對不是台灣
作家,他在台灣只待 7 天然後就到美國,他怎麼會是台灣作家?他的血緣不是,
他沒有在台灣有長期的活動。但是從另方面來說,他的出版基本上是在台灣,1968
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在台灣出版以後,後來他的全集甚至於更多的史料都是
在台灣,然後出版以後,讓他重新活了起來,然後我們談張愛玲太多太多的影響,
所以文學史不能不寫張愛玲,但他不是台灣作家。所以這樣講的話,哈金,你丟
給我們的問題,是不是也能順著這樣的觀點來討論,如果哈金的譯本基本上都是
台灣譯者譯的,在台灣出版,那他的中文文學活動主要是在台灣,他的影響是那
麼大的話,將來的台灣文學史當中,有心人可能會把他寫在台灣文學史裡面,但
我們能不能說他是台灣作家?
單德興老師: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不是台灣文學研究者,不過先前在這邊演講
過的陳國球老師,他的〈《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曾提到收錄的判準,
其中提到「影響」,所以張派的影響可能也是收錄的原因。其次,文學史一般希
望兼容並蓄,所以也會比較包容(inclusive)。第三,如果大家留意的話,我剛
剛演講的 PPT 中提到哈金是「中國作家」或「台灣作家」時,後面都加了一個
問號,因為相關答案涉及不同人的各別判準,而我身為台灣文學與華文文學的關
心者,以及譯者與翻譯研究者,有意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介入台灣文學。最後,
不管是高行健還是哈金,如果沒有台灣,他們的作品就無法如此全面地出版,由
宏觀的華文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在華文文學的文化生產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
陳萬益老師:我再問一個問題,因為講到台文是否應該研究翻譯的問題,我反過
來問說請問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之後,比如說是在中學的語文教育裡面,是應該
擺在所謂的國語文課程去呢?還是放在外語課上去上?為什麼?如果選擇放入
會有什麼問題?
單德興老師:以教科書為例,我們小時候的國語課本收入了〈最後的一課〉等作
品,可見當時的教科書已經納入了外國文學中譯,主要的用意應是要擴大學生的
視野。
陳萬益老師:如果是這樣子,台灣對翻譯的不重視就是外文的譯者不重視翻譯的
教學,我講的是在語文教育,因為我們上了大學之後,教英文的老師一定要你讀
英文、教日文的一定要你讀日文,卻是不讀翻譯的作品,所以你就是要讓台文、
中文系的不懂英文日文的去上翻譯,去閱讀翻譯的作品。你剛剛提到〈最後一課〉,
我講一個例子,我編過高中國文,當時我就考慮到高中國文裡面為什麼沒有外國
文學翻譯作品的空間,我努力要選一些翻譯的作品進去,後來選了一些作品很多
老師說這是新的我們不會教,後來我就找到〈最後一課〉還是胡適之翻譯的,可
是這個版本用了一年,後來高中老師向出版社反映,如果明年不把這課取消的話
就拒用這個版本。
廖詩文老師:我想分享一下在東大的學習經驗,當時老師是用夏目漱石的《心》
作為翻譯對照研究的文本,老師上課的時候,會印出《心》的多種外語版本,然
後和學生討論翻譯的問題。首先,老師會先說明夏目漱石《心》的時代背景、《心》
這部小說中不斷出現的關鍵詞是什麼,進而談《心》何以是能代表日本現代主義
的文學,作品中可以從哪裡看出夏目漱石想要反射出明治知識分子的鬱悶之處。
然後,老師會透過不同譯本的對照,解析在作品當中有非常多的關鍵詞,像是鬱
悶、寂寞這些在當時知識分子內心時常出現的情感,引導學生觀察在外國譯本裡
面是如何呈現,進而讓學生了解在跨文化的語境下,外國人是如何認識日本的現
代主義文學、如何看待夏目漱石的《心》。
以中文來說,在中文的語境下,我們一般比較不喜歡相同詞彙一直重複,但
是日文中若是不斷重複一樣的概念、一樣的詞語,在中文語境下該怎麼去翻譯,
方能讓夏目漱石所要反照出來的知識人的情感,如實再現在外語譯本上?在中文
的脈絡中,我們要怎麼去看待夏目漱石使用這些詞的意義?為了突顯這一點,夏
目漱石在原作上用了哪些字?而英文、中文、德文譯者又是怎麼翻譯這些詞語?
世界各國的讀者透過不同的外語譯本,會如何了解東方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
界?一個語言文化裡面,會有多少字詞可以描寫鬱悶?這都是可以從語言的檢視
與比較上,幫助我們重新了解原文,同時也能了解其他語言文化的一種比較性的
翻譯研究方法。
這種作法在台灣比較少見,要在高中進行難度也很高,不過我覺得有做過這
樣的對照練習很好,因為學生可以透過不同文本、而且是多語的比較與對照,深
刻地進行跨文化的認識,而不只是在溝通層面上進行平面性的跨文化理解。但是,
要在高中以這樣的方式上進行翻譯教學是不容易的,在大學方面,目前的翻譯課
也大多是從語言教學的面向切入,而非從文學研究或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切進,因
此也很難在外文系進行類似的翻譯教學與討論,這是對於翻譯的教學途徑及教學
目標不同所產生的結果。
單德興老師:我講兩點。首先,陳老師講的外文系不重視翻譯,我不很清楚現在
的情況,不過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翻譯是必修課。第二是譯本應用,我曾經跟一位
耶魯大學教授討論過,兩人都認為翻譯是練習外文的最好訓練,而且雖然訓練外
文時最好直接看外文,但好的譯本,尤其是譯注本,能協助學生掌握文意。再以
我自己為例,我們唸大學時,以當時台灣的英文訓練,其實要直接閱讀美國文學
經典有很大的困難,那也是為什麼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翻譯對我們那麼重
要。所以我跟那位耶魯教授的結論是:好的譯本,尤其是好的譯注本,確實能夠
幫人更深入了解、思考,或者激發學生見賢思齊。
至於好譯本的效用,我舉兩個切身的例子。第一,我翻譯過薩依德兩部作品,有
一次我遇到一位台大歷史系的年輕助理教授,他跟我說他到美國上研究所,在課
堂上討論薩依德,美國同學很奇怪為什麼來自台灣的他對薩依德相當熟悉,他跟
我說那是因為我的翻譯本除了譯文之外,還介紹了文本的背景與脈絡。另外,有
一位靜宜大學的畢業生到加拿大攻讀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研究的領域是新古典主
義時期,所以就帶了我譯注的《格理弗遊記》出國,結果發現譯注本不單對他身
為博士生有幫助,甚至對他當助教的教學都有幫助。其實,我在做翻譯的時候,
包括我們當初向國科會遊說成立經典譯注計畫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厚植國
家的軟實力或者華文世界的文化資本,所以越多人可以透過翻譯普遍吸收新知的
話,就越可望在知識或軟實力方面能夠有所提升,雖然我們並不能很明確地說那
些提升會在什麼時候出現。那也是我們願意投入翻譯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敢說自
己有多大的使命感,但是我們從前輩學者身上──比方說余光中老師、齊邦媛老
師等──確實吸收到很多的養分,也學到很多做事的方式、態度、嚴謹度,產生
了許多有形、無形的效應。身為受益者的我們,也希望能貢獻專長,把這個火炬
傳下去。
陳萬益老師:我對三位有很高的期待,剛剛在談比較文學,其實當年台大成立博
士班的時候,比較學系博士班,是外文跟中文合辦起來的,那時候我會讀一點英
文書其實是在中文系裡面聽了王文興,然後高級英文是齊老師來上,這些都有些
刺激,然後外文系要讀中國文學史,所以在某一方面來講中文外文是有交流的,
那如果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講,我請教各位一個翻譯教育的問題,我們的小孩子
在小學階段的時候會看很多外國翻譯的童畫看很多繪本,請問,他上了國高中,
剛才我們知道翻譯越來越少幾乎被掐死掉了,然後上了大學上了外文系他完全不
讀中文的書,不讀中國文學不讀台灣文學,那念了中文的對外文其實不懂,所以
翻譯剛好在這中間,所以如果我們要把翻譯的地位、重要性跟他的影響在台灣開
展出更大的格局來說,那恐怕經典的譯本也就是三位所作的不應該都是我們不懂
外文的人在念的,我那麼認真的讀單老師翻譯的《格理弗遊記》,請問外文系他
們懂外文為何要讀你的譯本,現在的觀念是這樣子,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把翻譯
在整個教育、語文、文學的體系裡面把他能夠擺進去的話,那還是學院的經典根
本只是文本而已嘛。
單德興老師:我很快回應一下。這要看老師而定,像在台大外文系教書的王安琪
教授,她教 Gulliver's Travels 時特地要學生去看我的譯注本。另外,我很高興陳
老師這麼看重翻譯與譯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翻譯與評介》新書分享會的主
題訂為「向譯者致敬」,因為譯者的貢獻與地位經常被抹煞,所以要鼓吹提升翻
譯的地位的同時,也應提升譯者的地位。
李育霖老師:我剛剛聽到現在其實我有很多話要講,不過時間的關係我簡單講,
因為我自己在美國比較學系教過課、在英文系與台文系所教過課,翻譯也是我主
要的(研究與教學),我現在也在學韓語及其他語言。不過我想陳萬益老師剛剛
提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翻譯不被重視,我覺得在高等教育,我講美國的例子,
因為我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因為他們是帝國,那我們台灣應該怎麼去設定人文
教育的目標,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在比較學系,我們要去上類似我們大一國文的
課,但他們叫語文課,美國的教育基本分成三大類:數學、邏輯、語文,所以他
們去判斷一個人的學習成果就是依這個標準,像比較學系我們開一個課叫世界文
學,其實世界文學有六大塊,收錄中國、日本、印度的文學等,他們設計這樣的
課程是希望他們的大學生有世界觀,所以這比較是文學的訓練和視野的開拓。我
贊成陳老師的說法,所謂的語言教育,不過我們是國語長期以來的殖民者意識形
態的塑造或語言的學習,所以基本上跟美國是不同的,我們的情況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總的來講,我還是覺得過去強調中文跟英文,再來強調白話文、強調台灣文
學、現在又要強調世界文學的脈絡,我覺得這個方向是肯定,但階段性的發展情
形還需要注意。另外翻譯的功能,我想在座的我們都是讀翻譯(作品)長大的,
甚至在高中學校沒有提供我們人文的需求,我們讀那些存在主義小說等其實是透
過翻譯的。(教書以後)在英文系,我們偷偷帶進去王禎和的東西,在成大台文
系的時候我必須負責西洋文學史,那我用原文上,其中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希望
同學去接觸到英文,一方面希望能夠看到世界文學從希臘開始教,一方面也是強
迫他們讀原文。所以這是個案例,就看老師的目的是什麼。
不過講到比較文學我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說,就是在比較文學的論述裡面,通常我
們會去要求還是去讀原文,你要有能力去翻譯,但是你不去翻譯,也就是說有能
力去讀原文,但做為一個比較文學者,他是有能力去翻譯但是不翻譯,因為很多
東西在翻譯當中會被抹煞掉。不過這是在博士生以上的層次,所以我想不同層次
的翻譯文學或者翻譯問題必須被考量但不能一概而論。
紀錄者:姚旟荃
陳芷凡教授開場
台灣文學研究會自 2012 年籌辦第一屆,經過多年的努力直至今天舉辦第十
三次例會,本會籌辦的初衷是希望能夠結合更多跨校且跨領域的學者,一起來思
考如何讓文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讓台灣文學的研究發展出新的期待。
此次議會的主題是由本所同樣從事翻譯研究關切的王惠珍老師進行統籌,並
且邀請此次與會的三位講者,而這三位講者既是研究學者也是翻譯者。單德興老
師是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研究的領域為比較文學、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
與翻譯研究,而除了文學與文化論述之外,單老師也翻譯《知識分子論》及《格
理弗遊記》等譯作,同時肩負研究者以及翻譯者的挑戰與責任。李育霖老師為中
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台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所的所長,研
究的範圍是電影研究、生態批評和德勒茲研究,譯有《德勒茲論文學》、《德勒茲
論音樂、繪畫與藝術》等,李老師是將德勒茲這位理論家的論著與理論概念介紹
給台灣讀者的重要推手。廖詩文教授是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副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翻譯理論、中日比較文學還有影像翻譯與視覺文化,廖
老師近來關切的議題是日本重要的文學家,例如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以及三浦
綾子文學在台灣翻譯的情形。
在惠珍老師的促成之下,這三位本身從事翻譯,同時也是翻譯理論傑出且重
要的研究者聚集在這裡,一起就翻譯文學與跨文化的命題展開更多元的對話。
一、單德興教授—談譯者余光中以及華美作家哈金
翻譯之必要,譯者之必要
余光中老師因為詩歌和散文的成就高超,以致許多人都忽略了他身為譯者的
貢獻。余老師提及譯者的時候曾說,「譯者未必有學者的權威,或是作家的聲譽」,
但是他特別推崇「翻譯」以及「寂寞之譯者獨享之特權。」然而,他也指出一般
譯者的實際情況卻是「往往名氣不如作家,地位又不如學者,又常常無利可圖,
而且稿酬偏低,無利可圖,又不算學術,無等可升,似乎只好為人作嫁,成人之
美了。」在場的三位講者都曾翻譯過專書,對於以上的說法應該特別能夠感受。
根據單德興老師(以下稱為講者)的經驗與理念,翻譯不應該只是文字的翻譯,
也應該把文字、文本之後的相關文化、歷史脈絡帶入其中,也就是原作、作者及
其脈絡的關係之外,還有進入另一個文化時可能產生的新意或效應,這也就是他
所提倡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的觀念。
在陳芳明老師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所編的余光中資料彙編1 中,談到余光中與
翻譯的只有金聖華老師的〈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譯家〉,由此可見對於譯
者余光中的相關研究非常少,而講者這幾年特別著重在這方面,已發表數篇論文
與一篇訪談。余光中老師除了身為學者、譯者、作者三「者」合一之外,張錦忠
1 陳芳明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34:余光中》(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也提到他是「五譯並進」:做翻譯、論翻譯、評翻譯、教翻譯、編譯詩選集。講
者則補充了另一譯,指出余光中老師多年對於翻譯的提倡不遺餘力。
從 1956-1957 年的《梵谷傳》2一路到王爾德所有的喜劇、2012 年的《濟慈
名著譯述》等,余光中老師的「譯績」多元而繁富。就譯出語與譯入語而言,既
有英翻中,也有中翻英;就文類而言,既有詩歌,也有小說、傳記;在工作方式
上,主要為獨譯,但也有合譯;有他譯,也有自譯;有單篇發表,也有連載、出
書;既有單一作家的文本,也有合集;既有他選,也有自選;既有中文文本,也
有英文文本,以及中英對照本;既有縱貫數世紀的詩作,也有十九世紀經典美國
文學,以及現當代的美國小說與中、英文詩作。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翻譯家的
養成不易。他的譯詩相當多元,從翻譯英詩中學到的內容、意象、形式都對年輕
詩人余光中有相當大的啟發。他自己也提到翻譯與創作之間密切的關係,主張譯
者要努力兼顧譯作的形與義。至於翻譯當中的歸化與異化,余光中比較傾向於歸
化,但也不全然排斥異化,因為異化能增加中文的表達方式。此外,他很明白再
好的翻譯也是能挑毛病的,因而提出「譯無全功」之說(Translation knows no
perfection.)。余光中從事翻譯工作將近一甲子,這種毅力與堅持非常值得我們敬
佩與學習。
哈金出生於中國遼寧,快 20 歲才開始學英文,1984 年取得山東大學英美文
學碩士學位,1985 年赴美留學,1992 年取得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博士學位。1989
年因為天安門大屠殺而決定留在美國,並選擇以英文從事文學創作,其後陸續獲
得美國眾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學獎項。身為使用非母語寫作的創作者,哈金先是出
版詩集,直至 2015 年才出版第一本中文詩集《另一個空間》。在例會中講者把哈
金的小說與譯作列出,並且提出了為何哈金未被納入台灣文學研究當中的疑問。
翻譯能不能列入 Sinophone studies(華語語系研究)?講者作為一個譯者以及翻譯
研究者,希望能夠從不同角度以翻譯來介入文學,一方面擴大文學研究的視野與
領域,另一方面也擴大翻譯研究的視野與領域。在哈金的漢譯作品中,有他譯、
自譯以及合譯,即使大多為他譯,但哈金都參與校訂,由此可知他在翻譯自身作
品當中的介入甚深。就他的身分來說,說他是華裔美籍作家、離散作家應無疑義。
但他能算是華語語系作家嗎?講者主張要將其放入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脈絡
中,這樣能夠 Sinophone studies 的領域擴及中譯的文本。那他能夠算是中國作家
嗎?講者舉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例子說明。中共官方主張高行健不是中國
人,法國人則是欣然接納高行健為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哈金的作品都在
台灣翻譯、出版,在大陸卻大都被禁止,那他能夠算是台灣作家嗎?單老師留下
這個課題等待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者來思考。
講者接著提到翻譯文學研究中多元系統(polysystem)的問題,特別是翻譯文
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當翻譯文學並非處於華文文學的首要或中心位置時,
哈金的作品依舊不斷地被翻譯成中文,因此華文世界對哈金的青睞是不能否認的
事實。如果翻譯作品在華語文學中有如一道光譜(spectrum),講者提出四項判準:
2 《梵谷傳》上、下冊分別於 1956、1957 年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作者是否為華人,二、寫作題材是否與華人有關,三、作者是否通曉華文,
四、作者在其作品翻譯過程中的介入程度。這四點將中譯文本納入 Sinophone
studies 的標準做了定位,而以這四個條件來看,哈金的作品確實能夠納入
Sinophone studies 當中了。
翻譯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關係,講者舉自身翻譯的《格里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為例,林以衡博士在做相關研究的時候,翻閱台灣日據時期的報紙發現
《台灣日日新報》就已經翻譯〈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而且報上還有序言,
這就代表此書的翻譯很早就進入台灣了,而且若非台灣文學研究者的努力,大家
就沒辦法注意到。
最後單德興老師提及理論的旅行與翻譯問題。陳芳明老師曾說「盡信理論,
不如沒有理論」,而講者則進一步主張「盡信理論,不如了解理論」。講者在翻譯
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文本時,將其理論的翻譯帶入華文世界的脈絡中,
希望薩依德的翻譯在中文世界不只是一個譯本,而是能夠確實向下扎根。賴慈芸
老師也將戒嚴時期的台灣翻譯史作了追蹤整理,完成了《翻譯偵探事務所》。3 講
者進一步表示,譯者的角色包含了中介、溝通、傳達、介入、操控、轉換、背叛、
顛覆、揭露與掩蓋、能動與反間、重製與取代等等。譯者不只是再現原作,也再
現了自己;而譯者同時也是益者,因為好的翻譯對作者、讀者、雙方文化和譯者
本身都有益處,是連結兩個語言與文化之間的橋樑。單德興老師強調台灣的比較
文學若要再出發,必須加強台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匯通,開啟彼此更廣闊的視野
與願景。
二、李育霖教授—談 Sinophone/Sinoglossia 的問題,以夏曼藍波安為例
台灣文學作家因為被殖民的關係,一拿起筆就活在翻譯當中,而做為一個第
三世界的人民,當書寫時本身就有翻譯的難題,而翻譯帶出來的,則是台灣文學
美學風格以及主體構成,甚至是倫理、或是如何生存的問題。而李育霖教授(以
下稱為講者)要談的是關於 Sinoglossia 的問題。從 Sinophone 開始談起,Sino 本
身就帶有殖民遺產命題並與之連結,而李育霖教授將 Sino 譯作為「華」,本身與
Chinese「中國」區分開來,也就是 Sinophone literature 與 Chinese literature 兩者
的區別。兩者在北美學界的脈絡中,已有區分,而所謂「語系」也與 Mandarin(普
通話)或是漢語的指稱不同了,這樣的論述同時也帶有中心/邊緣
(central/peripheral)、統一/碎片(united/fragmentary)、統一性/延異性
(unity/divergence)等對偶關係。這樣看來,史書美 Sinophone 的概念在台灣與後
殖民的概念連結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依舊充滿爭論,而王德威老師所談論的
Sinoglossia(華夷風)的概念,則是從中華文明脈絡一貫而下的華夷之別。
講者則是期待能夠從語音的角度將聲音放入 Sinophone 的文字當中,強調音
與文字之間的張力,不管文字是哪一種,於是他企圖發展 Sinoglossia 的論述。
Glossia 也就是拉丁語當中的語言的意思,Heteroglossia 眾所皆知的巴赫汀的眾聲
3 賴慈芸,《翻譯偵探事務所》(台北:蔚藍文化,2017)。
喧嘩,當中強調語言不是單一的,而是有所謂分歧的力量,這個分歧理所當然的
有一個中心(例如政府的規範),而日常用語當中又有離心的張力;而 Hetero 則同
時有傅柯的異托邦的概念在其中。講者企圖用此發展出 Sinoglossia 的雛型,而
glossia 指的是語言以及聲音本身,也在這裡我們從這裡看到翻譯的介入,
Sinoglossia 不只是語言的問題同時也是翻譯的問題,因此講者將 Sinoglossia 翻譯
為「華迻論」,這個「迻」字有翻譯的意思,包含了時間上的遷徙、民族的遷徙
以及跨國性的遷徙,而在《說文解字》中,「迻」則有翻譯(迻譯)的意思,他
再度強調 Sinoglossia 是一個語言的問題,同時也是翻譯的問題。
那如何看到翻譯呢?翻譯從字元來看就是把一個語言放在另一個脈絡當中,
是一種搬運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種重複。當我們在讀譯本的時候,即是一種重
複,在講者的認知當中翻譯是一個事件,是一次的重複性而不能被約化成一種再
現而已,而是一個行為。另外也要注意到翻譯的必要以及不可能。講者繼續以夏
曼藍波安為例,說明翻譯的相關問題。夏曼將達悟語與中文並列產生怎麼樣的效
果呢?兩種文字各自獨立的並列,並不直接指向中文翻譯,相反地,將讀者引入
一個巨大的空白、完全陌生的世界。
翻譯如何介入夏曼藍波安的書寫呢?先將中文文字放進括弧當中:「katwan,
katwan」 (飛魚,快來呀!快來呀!),或者是先用中文寫出達悟語,後再括弧
用中文解釋:「老人的太陽很低了」(歲月催人老,往事不堪回味),這樣的翻譯
介入成為一種雙語的不斷錯位詮釋,還有另一種「交換式的翻譯」:「我肉體先前
的靈魂」(先父,先母),成為達悟語的特殊用法在中文當中文字的轉換,而更深
一層交換,例如“mi kongkong si “ (達悟語,被恭喜之意),可以看到恭喜的意思
介入了達悟語當中,這些交換的過程不只是語言上,而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交換。
而翻譯當中的 Translingual(所謂的跨語的實踐),表現出來的是跨語的書寫,在翻
譯當中是一種結合、糾纏、混雜的表達,包含了字彙的、構句的、句子的、文法
的融混表達,舉例來說:「許老,海流會帶你回大陸。Kak mamoayayipasalaw so
pahad. (願你的靈魂如燕子般的善良)」,這個構句就是上述許多翻譯的作用,
也是跨語的實證。而在語言與文化上的接觸和衝突則是在《老海人》當中,國民
政府要求達悟耆老慶祝雙十國慶的情況更為明顯,那些「中華民國萬歲」式的吶
喊對達悟耆老來說是陌生的、無法理解的語言,於是以鬼吼鬼叫來呼口號,彼此
聲音的不協調成為一種聲音與吶喊的對峙,對彼此來說都沒有內容的聲音,因為
無法與語意做連結而造成衝突,翻譯者在這裡的作用則是粉飾雙方的語言並且弭
平衝突,雖然看似縫補語意的裂縫卻也擱置了文化的衝突。
三、廖詩文教授-談朱天心的《古都》日譯本
廖詩文教授首先談台灣文學的翻譯問題,他不只是關切外國文學在台灣的影
響和發展,也關心台灣文學輸出的議題,於是做了公部門外銷台灣文學的考察,
發現文建會時期和台灣文學館時期的公部門外譯情形有些不同。文建會時期外譯
推廣的文學類型包含了中國文學(例如史記等),且以英文譯作為大宗,並有較
多男性作者的作品,而台灣文學館接手後的外譯作品,則以日文較多,並以具有
更強的台灣文學主體意識作品為主,女作家作品也占了大部分,顯示出外譯至日
文的作品和英譯本在選書的考量上有所不同。講者提到這與翻譯贊助人、意識形
態、政治等等的因素有關,種種因素皆會導致英文讀者與日文讀者對台灣的想像
有所差異。而這也使得講者開始注意女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在日文當中被再現與
翻譯。
《古都》是記憶之書,以個人記憶納入歷史的記憶,是朱天心構築的烏托邦
世界,與川端康成的《古都》同名,那這兩者的互文性當然是在翻譯過程當中需
要注意的。這裡的互文性不只是出現在書名上的互文而已,內容上,包含地景、
生活上的描寫,朱天心的《古都》也都不斷與川端康成的《古都》互文,小說的
「虛構」與其外的台灣地景地物存在的「真實」也不斷互文。可想而知,譯者在
翻譯時就必須先對川端康成的《古都》有所了解、對朱天心描寫的台灣地景變遷
有所認識,方能翻譯得好。
清水賢一郎作為朱天心《古都》唯一的譯者,在翻譯時,展現出他仔細考證
朱天心文本內容的專業性。清水賢一郎的翻譯,段落上採原文尊重主義,在形式
上並未更動原文的結構、段落的再現,而在遣詞用字上,則採譯文尊重主義4,
使日語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能更容易理解句意。雖然某些地方並非直譯,但是保留
了原文的意象,使得譯文在日文當中更為流暢,而若是原作中獨特的台灣地景、
時空等等的描寫(對日本讀者來說的異文化),清水賢一郎便會保留並加以標音,
讓朱天心的異文化互文風格更為突出。此外,清水賢一郎在日譯本上增加許多譯
註,使《古都》日文版在考據上顯得更為細緻,甚至可以作為原著的參考書目。
《古都》日文版與中文版是用一種鏡像互文的方式,將朱天心的《古都》順
序重新排列,成為作者與譯者共同記憶的鏡像反射,而因朱天心又與川端康成的
小說內容彼此互文,這三者於是成了多菱鏡的折射關係,篇章的重新排列,使得
譯者也在翻譯上凸顯了其譯者的身分。
此外,因為日文沒有未來式,而是會在需要之處,或以現在式表達未來,或
用現在式表達過去,或用過去式表達時間,但這些時態與時間其實並沒有直接關
係,因此在翻譯的同時,譯者需要清楚了解原作中時間的穿越關係、空間的位移
關係,這樣才能使得日文句式準確表現出原作的語意。日文句子上主體改變的同
時,某些時間就會變動,再加上日文當中的主體若是遇到第一、第二人稱的時候,
往往可以加以省略,於是你/我的分界也會更模糊,中日語言結構上的差異性,
在碰觸到刻意模糊你/我身分與喜愛穿越時空的《古都》原著來說,日文譯者如
何掌握譯本的時態句構,就成為值得關注的研究項目,特別是在原作與翻譯間必
然存在詞語、句子不對等與無法跨越的難題上。
講者特別強調日本在進行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時,有時會從觀察譯者採用譯
文尊重原則還是原文尊重原則的方法切入。上述的觀點,與異化或歸化的分類略
有不同。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實務上往往無法全採異化或歸化的方法,而多是在
4 譯入語文化怎麼表達,就怎麼翻譯。
尊重原文或尊重譯文的原則下,透過譯者的巧思,適當傳達原作所要表達的意象;
而在翻譯之間發生哪些變化、為何如此變化,則就值得探討而成為比較文學研究
上關心的「有趣」議題。
透過《古都》譯本的解析,譯者表示除了可以看出朱天心在原作上刻意把你
/我、你們/我們刻意模糊化的書寫技巧,也可看到日文因須釐清主詞才能清楚
指陳作品中所要表達的主題,因此在譯本上,你/我、你們/我們反而在某些時
候必須被凸顯出來。這也會造成日文讀者和中文讀者在賞析《古都》時,分別會
有不同的閱讀樂趣及體驗,同時也讓我們再次確認了在不同語言的轉換上,主體
敘事會因不同語言表現而有難以跨越的藩籬。但在《古都》譯本上,譯者的考察、
對原作的深入、譯註的撰寫,確實讓日語讀者更容易了解作品的內容。
重點討論
王惠珍老師:針對李育霖老師談到夏曼藍波安的文本,夏曼的文本其實也有日譯
本,那日譯本是如何去翻譯夏曼的語言,翻譯再翻譯的問題要如何詮釋,這變成
了一種重譯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說,葉石濤先生在翻譯韓國文學的時候他並不懂
韓文,但將日本學者翻譯韓文的文本再翻譯成
卜生為例,他本身寫作的挪威語是個小語種,所以很多國家翻譯他的作品都是透
過英譯本,這是不得不的作法。另外,就目前的國際市場來說,很多翻譯作品都
是先有英譯本,在參加國際書展引起其他語種的出版社注意後去接洽版權,而後
再從原文直接翻譯成英文之外的語文,所以雖然還是直接從原文翻譯,但卻是透
過了英文的中介。其次是理論的翻譯,現在很多文學與文化理論都是來自大學出
版社的英譯本,理論上應該比較可靠,其實未必。這裡舉兩個例子。一個就是李
歐塔的《後現代情況》(Francois Lyotard, Postmodern Condition)英譯本,有熟
悉內情的歐洲學者告訴我,這本書上掛了兩位譯者的名字,實際上兩人根本沒有
合作,而是原譯者的翻譯不能用,只好使用後面譯者的譯本,但又不能讓原譯者
感到白費工,所以掛了兩個名字。另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就是,彭淮棟直接從德文
翻譯《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Beethoven: Philosophie der Musik [Beethove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並在〈譯跋〉寫到,雖然他直接譯自德文,但在參
考英譯本和簡體字版的中譯本時發現,英譯本中的誤譯(否定詞沒有翻譯)導致
從英文轉譯的中譯本也隨之誤譯。因此,彭淮棟必須特別在〈譯跋〉中指出來,
免得別人對照英譯本而認為彭譯是誤譯。此外,柳書琴老師剛剛跟我提到,有佛
教團體要將藏文佛經翻譯成中文或英文,而藏文佛經本身是從印度梵文翻譯,梵
文的原文可能早就不見了,所以原本是譯文的藏文佛經就成了唯一的原文,再翻
譯成中文或英文時就變成是再翻譯。中文裡也有類似的情況,比方說梵文經典翻
譯成中文後,原來的梵文經典迭失了,或者也許還在但已翻譯成藏文或英文,若
要比對的話需要具有多語文的能力,所以牽涉到翻譯或再譯的情況。最後一個例
子是,我翻譯聖嚴法師在美國主持禪修時的禪堂中文開示,一方面是法師將禪宗
祖師大德的文言著作翻成白話,這就是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另一
方面是現場有專人口譯成英文,又牽涉到口譯(interpretation)與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後來經由錄音之後的整理謄抄,從語音文本變成文字
文本則是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之後編輯出版成英文書,再由筆
者翻譯成中文書,所以這裡比剛剛說到的重譯或轉譯更加複雜,既涉及中翻中的
語內翻譯,也涉及中翻英與英翻中的語際翻譯,更涉及返譯(back translation)
或雙重返譯(dual back translation)。因此,翻譯是變化多端的藝術,而這也是
翻譯好玩、有趣的地方。
李癸雲老師:從李老師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夏曼‧藍波安在創作的時候,是
先用達悟與寫下他想寫的之後再翻譯成中文,那他到後期比如說《老海人》這樣
長篇的著作一樣也是用同樣的創作方式嗎?或者說他常常在臉書發表自己的看
法,連這樣子的創作方式也是透過翻譯嗎?那假設他必須都要通過這樣的程序的
時候,李老師也提到就是說,達悟族的語言有它背後的一些思想、文化甚至祖靈
信仰、種種的語音等很特殊的表達方式,可是當他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夏曼只能援
用他如何被中文這個語意系統所訓練的東西來翻譯,所以他用的是華語或者中文
的邏輯、文化等,那當然你肯定在翻譯過程當中,可能有滲透的部分,尤其是在
語音滲透或者是用語的變異等等,可是如果我現在又是一個讀者在介入這個過程,
閱讀理解這些作品的時候,是不是也是一種意義的翻譯?那這個讀者如果不是跟
夏曼在相同的達悟思想底下的時候,他所能萃取到或理解的或許都還是這個讀者
背後中文的語言系統而已,所以如果他有變異性或是被滲透、被改造華語的可能
的時候,會不會其實都被阻隔在文化差異之外?也就是說夏曼的那一套中文的使
用方式只能停留在夏曼,如果沒有跟他有相符合的、了解達悟的表意方式的人,
他所能理解的可能還是從中文的角度去看,而沒有去察覺那些特殊的、屬於達悟
族的東西。
李育霖老師:我簡短的回應一下。你覺得他寫的是(標準)中文嗎?你說,你用
中文的角度去讀,那你覺得夏曼寫的是中文嗎?
李癸雲老師:中文這個介譯是字符的問題嗎?
李育霖老師:這樣就變成如果你要去判斷什麼是中文,然後說夏曼是或不是(中
文書寫)?我剛剛講說,特別是在《八代灣神話》等剛開始創作的時候,因為他
對中文沒有把握,對達悟族語也沒有太大的把握,但是他寫的過程他自己講說他
還得必須用達悟族語寫下來,然後再翻譯成中文,因為他中文也沒有把握所以非
常的痛苦,這是早期的呈現。但你可以發現,他寫作的策略或者是翻譯其實是有
改變的,有時候他用翻譯的方式,有時候他用並列的方式,我想並列的方式有一
段期間,特別是他參加原住民運動的時候,意識到語言本身就標示著文化區位的
存在,所以他很刻意在中間那段創作時間特別都是用達悟語並列的。在早期其實
那樣翻譯是更明顯的,因為他嘗試把所有達悟語翻成中文,所以他很懊惱為何當
時不是用達悟語寫,所以這二三十年的創作他的內在其實是有變化的。
回到最後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他做為一個華語表述的形式,在形式上它產生
了變異,在語言內部或是書寫的符號本身都產生了變異,這是我的結論。至於你
剛剛的問題,如果你有所謂的標準的中文,那你就可以看到屬於變異的部分。就
像我剛剛講的,中文是分歧的、碎片的、在變異當中的。我並不像後現代主義者
去標榜一種語意或者符號的漂流,譯文仍然是對應原文,原文跟譯文之間就算我
們不知道原文,但像夏曼‧藍波安的文本,我們能夠在譯文中間看到原文,很多
台灣文學或理論是沒有原文的譯本,因為我們寫的是華語,但不是母語,所以原
文在譯文中,我們還是能在譯本當中讀到原文,所以原文跟譯文在生產中是不斷
交錯、摺疊的過程,這個摺疊的過程會產生新的東西。至於讀者能不能介入這樣
閱讀過程當然是可能的,像現在網路,或者是現在強調互動,我覺得這是個新的
領域,我目前還沒有辦法掌握那個部分,我想以此作為出發點,在所掌握的符號
或聲音裡面觀察到它的變異,去判斷台灣文學當中的特殊風格跟他內部的主體構
成,我想這是我關懷的重點。
許宸碩:老師你剛剛有提到翻譯的問題還有台灣文學,我就想到台語羅馬字,台
語羅馬字在華語語系當中會談到這個特殊的例子嗎?台灣之所以有很多文本翻
譯到日本,還包括兩國之間的政治互動,我們翻譯外語的時候是需要理論的輸入,
那我們有華語知識的輸出嗎?
李育霖老師:的確,在華語語系的研究當中的確沒有注意到台語羅馬字的問題,
但在華語語系研究當中,我們不是去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華語語系、那個東西是
不是華語語系,因而把華語語系視為一個範疇。對華語語系的看法各有說法,但
台語羅馬字是不是華語語系,如果你覺得是的話你就去談談看,如果不是的話也
可以談,有些人認為華語語系的基本定義是所謂 Written in Chinese,根本的定義
是用中文寫的,那剛剛單老師也提到用英文寫的能不能算入華語語系,那當然如
果算入的話,定義就會改變,可能是一種族裔或者文化的概念了,所以重點不是
什麼東西是 Sinophone,重點是你的東西用 Sinophone 可以帶出什麼命題和什麼
思考的力度。
第二個知識輸出,我講個例子我與前輩老師聊天的時候常常提到,例如日本用四
代完成現代化的過程,第一代包含出去(出國)學習並且翻譯回來,第二代用外
國理論認識(本地的文本材料),第三代發展出自己的東西,第四代再把理論輸
出。回到台灣的知識輸出,史書美老師現在與一群學者在做的是台灣知識系統的
建構。我們的確是做為一個殖民地,我們吸收很多外來的東西,也派很多人去國
外輸入,所以覺得我們這一代特別辛苦,一方面又要翻譯、一方面又要拿西方的
東西拿來研究台灣的東西、一方面又要把台灣的東西搞出理論、再來又要把台灣
的東西提高國際能見度,所以四代的事情要壓縮在這一代完成。所以講說有沒有
理論輸出,西方正在很快速的輸出,那台灣必須更加緊速度來推動我們的思考、
知識系統或是思維方式。如果台灣的思維方式是特殊的,那自然世界就會來參考,
台灣的確在經濟歷史都有特殊的案例,所以都會有外來者來研究,台灣確實在很
多方面都不是太重要,但就是因為這個不是太重要在很多方面不佔有主流的知識
範圍當中,所以我們能夠創造出新的模式,這是我們社會所要追求的東西,我講
的很快而且夾帶著很多民族歷史的情感在裡面,但這是我們這一代承襲陳萬益老
師那一代的工作。
陳萬益老師:稍微來談台文所在講翻譯的問題,歡迎三位來台灣系所講比較文學
講翻譯等等的問題。那單老師剛剛在過程當中,可以說是向台文系所師生挑戰,
也可以說是在翻譯理論底下來談台灣文學的課題,那我先回答你台文系所有沒有
在做翻譯的研究,我沒有全面去了解,不過清華有一個碩士論文,是做日本時代
台灣翻譯的研究,比較具體的,他是拿賴和、楊逵、張我軍他們一批人來討論的,
賴和的翻譯他有翻譯尼采論文,大概是在他醫學校時候所作的翻譯,張我軍因為
後來他到北平,他的翻譯相當的多,因為他也從事日語的教學嘛!其中有一部我
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夏目漱石的文學論,這部書到台灣以後還沒有出來,也沒有看
到別的精通日文的人來翻譯這部書,據了解這是夏目漱石在那個時代,日本近代
文學史當中很重要的文學論,那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說,賴和在 1924 年跟張我
軍引發起來的新舊文學論戰當中,賴和就說過,「新文學是舶來品,所以帶有奶
油的味道。」。這個也就是那個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接受到外來
的思潮,外來的作品影響,開展了新文學的寫作。所以陳千武就說了台灣新文學
的兩個球根,在過去的幾個世代裡一直就講台灣新文學受五四影響,這不必否認,
但他另一個球根其實是從日文來接觸的外國文學的影響,所以前不久受到相當注
目的,講 1930 年代風車詩社,這個也是逐漸被發現整理出來的,原來我們台灣
在 1930 年代就有一個這樣的相當現代主義的詩社,有他們創作的成品,所以不
僅是在日本時代這一批在日本教育底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以至於到戰後,其
實他們也還在做翻譯,所以在台文系所當中作翻譯研究不是不可能,也是應該重
視的面向。
第二個問題你談到哈金,然後 Power point 當中你明顯的問說,到底哈金是中國
作家還是台灣作家?我想先請問你最後的結論。
單德興老師:我想這可能要留給各位台灣文學的專家和後起之秀來回答。如果容
許我舉一個例子。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中提到張愛玲,那張愛玲算不算台
灣作家?我想先請教您的意見。
陳萬益老師:因為你講哈金接著提到高行健,高行健曾經來清華大學做過專題演
講,柳書琴老師主持的,那場在清大大禮堂九成五都坐滿,從高行健談起。高行
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接到一通國外來的電話,韓國打來的,我台大的學
弟打電話來請我以最快的速度寄高行健的書給他,因為高行健在中國大陸基本上
是封殺,不承認他是中國作家,但是國外還是在看高行健,是看明星出版社出版
的作品,所以高行健我就說是台灣作家,如果是這樣講的話台灣作家就得到諾貝
爾文學獎了,這當然是開玩笑的。但是,你剛剛提到張愛玲是不是台灣作家的問
題,在 1999 年聯合報副刊選台灣經典 30 家將張愛玲選進去,後來陳芳明在經典
30 之後的會議也說張愛玲是台灣作家,台灣與會人強烈的抗議說張愛玲不是台
灣作家,為何聯合報將他選入台灣的經典,這個問題在台灣文學界一直議論紛紛,
當然你看到陳芳明的新文學史也寫進張愛玲,但被稱為台派的文學史經典葉石濤
的《台灣文學史綱》也把張愛玲寫進去,更特殊的是 2000 年成大台文所,葉石
濤先生在那邊講課,我們的客座教授下村作次郎就去聽、去錄音,有一天葉老講
張愛玲,下村跑來找我:「陳老師,葉老說張愛玲是台灣作家。」,我說怎麼可能,
他就把錄音帶給我聽。這個話題確實在 2000 年才開展起來的,台灣文學的體制
化作為一個新興學術領域當中,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斷,所以學生也會問我張愛玲
是不是台灣作家,我說當然不是啊,她怎麼會是台灣作家呢?但是台灣文學史有
寫進去啊,那為什麼他不是台灣作家?今天你今天講的剛好可以回答。哈金他是
中國作家還是台灣作家?還是華裔美籍作家?高行健是華裔法國籍的作家?如
果中國人高興說他是我們中國作家,如果台灣人因為他的書在台灣出版所以說他
是台灣作家,隨你高興啊,有什麼不可以?艾略特是美國作家還是英國作家?都
可以。就是說只要國人認同,他就是你的作家,如果我們往前推,台灣文學史的
寫作一開始就沒有問「你是不是台灣作家」,黃得時在 1943 年台灣文學史的序說
當中就這樣說,台灣文學史要寫哪些人哪些作家,他有一個關鍵詞叫文學活動,
文學活動在台灣的就把他收進來,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說,張愛玲絕對不是台灣
作家,他在台灣只待 7 天然後就到美國,他怎麼會是台灣作家?他的血緣不是,
他沒有在台灣有長期的活動。但是從另方面來說,他的出版基本上是在台灣,1968
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在台灣出版以後,後來他的全集甚至於更多的史料都是
在台灣,然後出版以後,讓他重新活了起來,然後我們談張愛玲太多太多的影響,
所以文學史不能不寫張愛玲,但他不是台灣作家。所以這樣講的話,哈金,你丟
給我們的問題,是不是也能順著這樣的觀點來討論,如果哈金的譯本基本上都是
台灣譯者譯的,在台灣出版,那他的中文文學活動主要是在台灣,他的影響是那
麼大的話,將來的台灣文學史當中,有心人可能會把他寫在台灣文學史裡面,但
我們能不能說他是台灣作家?
單德興老師: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不是台灣文學研究者,不過先前在這邊演講
過的陳國球老師,他的〈《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總序〉曾提到收錄的判準,
其中提到「影響」,所以張派的影響可能也是收錄的原因。其次,文學史一般希
望兼容並蓄,所以也會比較包容(inclusive)。第三,如果大家留意的話,我剛
剛演講的 PPT 中提到哈金是「中國作家」或「台灣作家」時,後面都加了一個
問號,因為相關答案涉及不同人的各別判準,而我身為台灣文學與華文文學的關
心者,以及譯者與翻譯研究者,有意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介入台灣文學。最後,
不管是高行健還是哈金,如果沒有台灣,他們的作品就無法如此全面地出版,由
宏觀的華文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在華文文學的文化生產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
陳萬益老師:我再問一個問題,因為講到台文是否應該研究翻譯的問題,我反過
來問說請問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之後,比如說是在中學的語文教育裡面,是應該
擺在所謂的國語文課程去呢?還是放在外語課上去上?為什麼?如果選擇放入
會有什麼問題?
單德興老師:以教科書為例,我們小時候的國語課本收入了〈最後的一課〉等作
品,可見當時的教科書已經納入了外國文學中譯,主要的用意應是要擴大學生的
視野。
陳萬益老師:如果是這樣子,台灣對翻譯的不重視就是外文的譯者不重視翻譯的
教學,我講的是在語文教育,因為我們上了大學之後,教英文的老師一定要你讀
英文、教日文的一定要你讀日文,卻是不讀翻譯的作品,所以你就是要讓台文、
中文系的不懂英文日文的去上翻譯,去閱讀翻譯的作品。你剛剛提到〈最後一課〉,
我講一個例子,我編過高中國文,當時我就考慮到高中國文裡面為什麼沒有外國
文學翻譯作品的空間,我努力要選一些翻譯的作品進去,後來選了一些作品很多
老師說這是新的我們不會教,後來我就找到〈最後一課〉還是胡適之翻譯的,可
是這個版本用了一年,後來高中老師向出版社反映,如果明年不把這課取消的話
就拒用這個版本。
廖詩文老師:我想分享一下在東大的學習經驗,當時老師是用夏目漱石的《心》
作為翻譯對照研究的文本,老師上課的時候,會印出《心》的多種外語版本,然
後和學生討論翻譯的問題。首先,老師會先說明夏目漱石《心》的時代背景、《心》
這部小說中不斷出現的關鍵詞是什麼,進而談《心》何以是能代表日本現代主義
的文學,作品中可以從哪裡看出夏目漱石想要反射出明治知識分子的鬱悶之處。
然後,老師會透過不同譯本的對照,解析在作品當中有非常多的關鍵詞,像是鬱
悶、寂寞這些在當時知識分子內心時常出現的情感,引導學生觀察在外國譯本裡
面是如何呈現,進而讓學生了解在跨文化的語境下,外國人是如何認識日本的現
代主義文學、如何看待夏目漱石的《心》。
以中文來說,在中文的語境下,我們一般比較不喜歡相同詞彙一直重複,但
是日文中若是不斷重複一樣的概念、一樣的詞語,在中文語境下該怎麼去翻譯,
方能讓夏目漱石所要反照出來的知識人的情感,如實再現在外語譯本上?在中文
的脈絡中,我們要怎麼去看待夏目漱石使用這些詞的意義?為了突顯這一點,夏
目漱石在原作上用了哪些字?而英文、中文、德文譯者又是怎麼翻譯這些詞語?
世界各國的讀者透過不同的外語譯本,會如何了解東方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
界?一個語言文化裡面,會有多少字詞可以描寫鬱悶?這都是可以從語言的檢視
與比較上,幫助我們重新了解原文,同時也能了解其他語言文化的一種比較性的
翻譯研究方法。
這種作法在台灣比較少見,要在高中進行難度也很高,不過我覺得有做過這
樣的對照練習很好,因為學生可以透過不同文本、而且是多語的比較與對照,深
刻地進行跨文化的認識,而不只是在溝通層面上進行平面性的跨文化理解。但是,
要在高中以這樣的方式上進行翻譯教學是不容易的,在大學方面,目前的翻譯課
也大多是從語言教學的面向切入,而非從文學研究或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切進,因
此也很難在外文系進行類似的翻譯教學與討論,這是對於翻譯的教學途徑及教學
目標不同所產生的結果。
單德興老師:我講兩點。首先,陳老師講的外文系不重視翻譯,我不很清楚現在
的情況,不過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翻譯是必修課。第二是譯本應用,我曾經跟一位
耶魯大學教授討論過,兩人都認為翻譯是練習外文的最好訓練,而且雖然訓練外
文時最好直接看外文,但好的譯本,尤其是譯注本,能協助學生掌握文意。再以
我自己為例,我們唸大學時,以當時台灣的英文訓練,其實要直接閱讀美國文學
經典有很大的困難,那也是為什麼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翻譯對我們那麼重
要。所以我跟那位耶魯教授的結論是:好的譯本,尤其是好的譯注本,確實能夠
幫人更深入了解、思考,或者激發學生見賢思齊。
至於好譯本的效用,我舉兩個切身的例子。第一,我翻譯過薩依德兩部作品,有
一次我遇到一位台大歷史系的年輕助理教授,他跟我說他到美國上研究所,在課
堂上討論薩依德,美國同學很奇怪為什麼來自台灣的他對薩依德相當熟悉,他跟
我說那是因為我的翻譯本除了譯文之外,還介紹了文本的背景與脈絡。另外,有
一位靜宜大學的畢業生到加拿大攻讀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研究的領域是新古典主
義時期,所以就帶了我譯注的《格理弗遊記》出國,結果發現譯注本不單對他身
為博士生有幫助,甚至對他當助教的教學都有幫助。其實,我在做翻譯的時候,
包括我們當初向國科會遊說成立經典譯注計畫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厚植國
家的軟實力或者華文世界的文化資本,所以越多人可以透過翻譯普遍吸收新知的
話,就越可望在知識或軟實力方面能夠有所提升,雖然我們並不能很明確地說那
些提升會在什麼時候出現。那也是我們願意投入翻譯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敢說自
己有多大的使命感,但是我們從前輩學者身上──比方說余光中老師、齊邦媛老
師等──確實吸收到很多的養分,也學到很多做事的方式、態度、嚴謹度,產生
了許多有形、無形的效應。身為受益者的我們,也希望能貢獻專長,把這個火炬
傳下去。
陳萬益老師:我對三位有很高的期待,剛剛在談比較文學,其實當年台大成立博
士班的時候,比較學系博士班,是外文跟中文合辦起來的,那時候我會讀一點英
文書其實是在中文系裡面聽了王文興,然後高級英文是齊老師來上,這些都有些
刺激,然後外文系要讀中國文學史,所以在某一方面來講中文外文是有交流的,
那如果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講,我請教各位一個翻譯教育的問題,我們的小孩子
在小學階段的時候會看很多外國翻譯的童畫看很多繪本,請問,他上了國高中,
剛才我們知道翻譯越來越少幾乎被掐死掉了,然後上了大學上了外文系他完全不
讀中文的書,不讀中國文學不讀台灣文學,那念了中文的對外文其實不懂,所以
翻譯剛好在這中間,所以如果我們要把翻譯的地位、重要性跟他的影響在台灣開
展出更大的格局來說,那恐怕經典的譯本也就是三位所作的不應該都是我們不懂
外文的人在念的,我那麼認真的讀單老師翻譯的《格理弗遊記》,請問外文系他
們懂外文為何要讀你的譯本,現在的觀念是這樣子,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把翻譯
在整個教育、語文、文學的體系裡面把他能夠擺進去的話,那還是學院的經典根
本只是文本而已嘛。
單德興老師:我很快回應一下。這要看老師而定,像在台大外文系教書的王安琪
教授,她教 Gulliver's Travels 時特地要學生去看我的譯注本。另外,我很高興陳
老師這麼看重翻譯與譯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翻譯與評介》新書分享會的主
題訂為「向譯者致敬」,因為譯者的貢獻與地位經常被抹煞,所以要鼓吹提升翻
譯的地位的同時,也應提升譯者的地位。
李育霖老師:我剛剛聽到現在其實我有很多話要講,不過時間的關係我簡單講,
因為我自己在美國比較學系教過課、在英文系與台文系所教過課,翻譯也是我主
要的(研究與教學),我現在也在學韓語及其他語言。不過我想陳萬益老師剛剛
提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翻譯不被重視,我覺得在高等教育,我講美國的例子,
因為我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因為他們是帝國,那我們台灣應該怎麼去設定人文
教育的目標,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在比較學系,我們要去上類似我們大一國文的
課,但他們叫語文課,美國的教育基本分成三大類:數學、邏輯、語文,所以他
們去判斷一個人的學習成果就是依這個標準,像比較學系我們開一個課叫世界文
學,其實世界文學有六大塊,收錄中國、日本、印度的文學等,他們設計這樣的
課程是希望他們的大學生有世界觀,所以這比較是文學的訓練和視野的開拓。我
贊成陳老師的說法,所謂的語言教育,不過我們是國語長期以來的殖民者意識形
態的塑造或語言的學習,所以基本上跟美國是不同的,我們的情況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總的來講,我還是覺得過去強調中文跟英文,再來強調白話文、強調台灣文
學、現在又要強調世界文學的脈絡,我覺得這個方向是肯定,但階段性的發展情
形還需要注意。另外翻譯的功能,我想在座的我們都是讀翻譯(作品)長大的,
甚至在高中學校沒有提供我們人文的需求,我們讀那些存在主義小說等其實是透
過翻譯的。(教書以後)在英文系,我們偷偷帶進去王禎和的東西,在成大台文
系的時候我必須負責西洋文學史,那我用原文上,其中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希望
同學去接觸到英文,一方面希望能夠看到世界文學從希臘開始教,一方面也是強
迫他們讀原文。所以這是個案例,就看老師的目的是什麼。
不過講到比較文學我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說,就是在比較文學的論述裡面,通常我
們會去要求還是去讀原文,你要有能力去翻譯,但是你不去翻譯,也就是說有能
力去讀原文,但做為一個比較文學者,他是有能力去翻譯但是不翻譯,因為很多
東西在翻譯當中會被抹煞掉。不過這是在博士生以上的層次,所以我想不同層次
的翻譯文學或者翻譯問題必須被考量但不能一概而論。